近几年我常常听人们拿王阳明和曾国藩为人推崇,说我们应该如何如何像王阳明和曾国藩一样做人做事,像他们那样治国理政。与此同时,人们又拿这两位圣人作类比,审视谁更完美一些。听了这话,我心里总觉得别扭得很!

其实,拿王阳明和曾国藩比谁更完美些,这是一个文化人格理解上的偏差。王阳明这个出生在余姚的学问家,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土地上的奇葩,他与孔子、朱熹、与曾国藩相比,自然格格不入,他要高一点,远一点,飘逸一点,他应该是一个天上飞的人。在这一点上很有点像文学家苏东坡一样,总是高翔于人生的云端;在哲学上更接近老庄一些。而曾国藩是一个在地上机警地行走的智者,他的十三部家书都是一些如何做人、如何做官之道的技巧,特别是那部《冰鉴》说的极为世故,我认真看了看,和现实生活对照一番,他的那套算命之术,实在是欺世盗名。如果以此来选拔任用一个干部,实在是误国误人!

把孔子、朱熹和曾国藩与王阳明统称为“圣人”,实际上是中国文化归类上的偏差和误解。前面三位老先生是一类,王阳明是另类。于曾国藩和王阳明来说,曾国藩的思想是为其做官服务的,“怎样做官”、“怎样做大官”、“怎样做稳官”始终是其考虑的核心问题,他的为民、忠君等都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

王阳明作为中国明朝时期的哲学家、军事家、政治家,其哲学思想被称为王阳明心学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知行合一”、“格物致知”和“致良知”。
知行合一。这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之一,强调人们常常知道应该做什么,但却不能真正做到。他认为,人的内心本身就有道德的指引,只要用心去感受就能理解事物的本质,从而能够真正做到。因此,他主张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理解道德的内涵,才能真正理解世界。
格物致知。王阳明心学倡导通过感知和实践来获取知识,认为人们只有通过直接感知才能真正了解事物的本质,才能理解自己的内心。因此,他主张人们应该通过实践来获取知识,而不是只凭借书本和传统的学习方法。
致良知。这是王阳明心学的又一个核心思想,他认为人们内心本身就有道德的指引,只要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就能够通过自我觉察来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他认为人的良知是一种自然存在的道德力量,只要人们能够真正意识到这一点,就能够自我完善,进而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

王阳明心学不仅为王阳明本人的哲学理论打下了基础,也对后来的中国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思想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世人的广泛仰望。
王阳明有自己的社会理想,对个人、国家、历史、社会等都有自己的看法。他的做官,是为实现自己理想服务的。当做官与这个理想有冲突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所以,从本质上讲,王阳明是个读书人,曾国藩是个官员。王阳明要高一点,远一点,超脱飘逸一点;曾国藩则近一点,实一点,世故实用一些。

然而,他们的本质区别还不在此。中国儒家学问的最高境界都是实用主义的,如修心、正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固然这没有错,而且能做到这一点就很不易和伟大了,已经很了不起!只是它的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实用主义的。世界万物,无直接有利于我的,我是绝不会干的!从历史创造上看,指南针、火药、印刷术、造纸、地动仪、万里长城等等无一不和实用有关,稍稍与实用远一点的是祖冲之,他的圆周率和我们一般人的生活并无多少直接干系。
当然,春秋战国的公元前230年出了个公孙龙,也是一个奇葩,这里我要多说几句。他的“白马非马”的确远离了人们的生活实用范畴,在一个理性意识中探索生命的意义以及社会结构的意义。他的《白马论》的基本论点是:“白马非马”。“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白马非马”这一哲学命题揭示了特定与一般、个别与普遍之间的关系,强调了在特定情境下,个别事物的属性并不等同于该类事物的普遍属性。

从这些论点中可以看出,公孙龙的确看到了一个命题中主语和述语的矛盾对立的方面,看到了一般和个别的差别。这就是公孙龙所说的“故可以为有马者,独以马为有马耳,非有白马为有马”。
看到这里我们就明白,这是一个永远可以辩论下去的命题,也是一个永远纠缠不清的哲学命题。它的价值不是社会实践活动中立竿见影可以看得见的理性思考,而是远离了人们社会生活实践的“高谈阔论”。
我的问题不是孰是孰非,而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实用主义的国度里,尽然出了这么一个奇葩,这个春秋战国的赵国邯郸人,居然以自己的生命之光,曾经照亮了中国偏隅一角!然而他的光辉很快被儒家思想压抑下去了,因为它的社会意义与治国、忠君、科举等等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就如同墨家的“非攻”、“爱人”一样,远离了君主思想和民众的诉求!

时至今日,有谁因为“白马非马”的问题,而孜孜不倦的探究和终其一生“钻牛角尖”呢?人们更注重当下的生活意义。做为正能量宣传的“赠人玫瑰,手留余香”、“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正是和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的生存命脉,和我们这个民族的实用主义理念紧紧相连,换句话说,就是“对我”没有直接好处的事,我是绝不会去做的!如像曾仕强先生的那一套学说,具有很大的实用性,很容易在中国人大众中找到思想感情和传统文化上的共鸣点,所以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和赞同。其实说到这儿,就已经回答了许许多多人千万遍问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中华民族为什么没有自己的信仰?为什么没有自己本土的宗教?”

因为宗教、信仰是高悬于人们现实之上的灵魂准则,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出现过像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都是天上飞的,(只有马克思才把理论从天上拽到了地下,才从“政治经济学”和“剩余价值”中把一无所有的劳动者的命运和哲学联系在一起);中国也没有产生过像哥白尼、布鲁诺这样的“犟骨头”,就因为争一个和自己日常生活毫无干系的“地球绕着太阳转”的说法,硬是死咬着不放,你烧死我,我还是这么说!这在实用主义、委曲求全,信奉儒教的中国人来说,不可思议。所以这才会在西方产生了雨果这样伟大的《悲惨世界》巨作,才会有了“世界上最浩瀚的是大海,比大海更浩瀚的是蓝天,比蓝天更加浩瀚的是人的心灵”的胸襟。千百年来由孔夫子、朱子、曾文公这样的文化滋养出来的人群,怎么可能产生高飞于人们心灵之上的“宗教信仰”的灵魂之鸟呢?我们不是近百年、近千年才落后的,我们在根子上、从始发点上就与西方有着南辕北辙的生命系统本质上的不同。

这里我们不妨看看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相对应时代的西方世界里几个典型的经典思想,也好做一点文明史上的比较!
出生于公元前427年的柏拉图在《理想国》里以数学的思维,来解释这个世界和宇宙。他的主要思想认为世界由“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所组成。理念的世界是真实的存在,永恒不变,而人类感官所接触到的这个现实的世界,只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微弱的影子,它由现象所组成,而每种现象是因时空等因素而表现出暂时变动等特征。由此出发,柏拉图提出了一种理念论和回忆说的认识论,并将它作为其“教学理论”的哲学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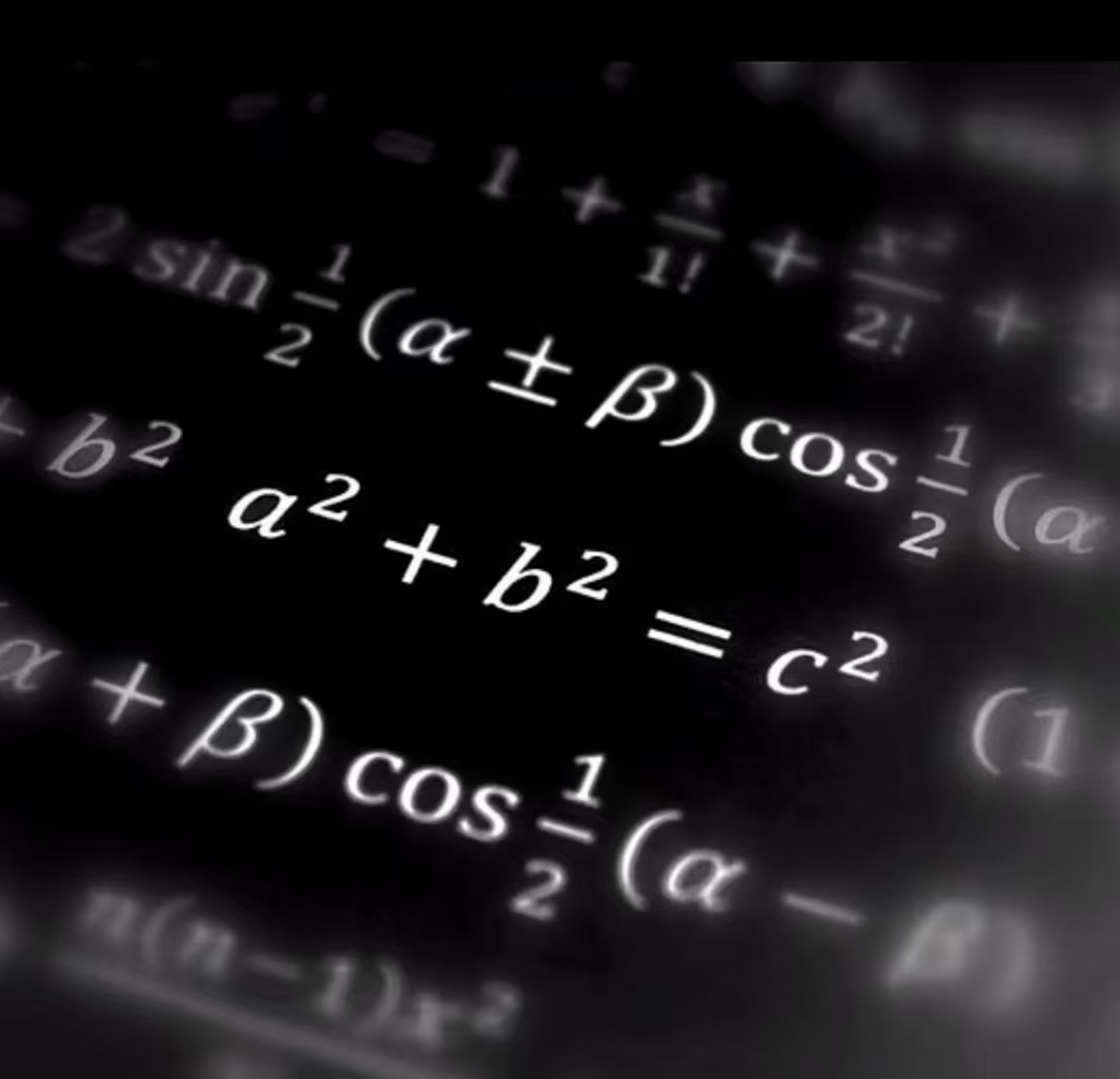
柏拉图认为人的一切知识都是由天赋而来的数学构成,它以潜在的方式存在于人的灵魂之中。因此认识不是对世界物质的感受,而是对理念世界的回忆。
就主要成就而言,柏拉图的这些理论是源于毕达哥拉在“数是万物本原”的数学哲学思想,潜心研究数学,给数赋予了很多特殊的含义,毕达哥拉斯认为六面体中包含有地球的奥秘,四棱锥中蕴藏有火的含义,十二面体中囊括有宇宙的神秘。还把数分为聪明的、愚蠢的、知足的、不知足的,并且给出了平均数、亲和数和完全数的概念。

毕达哥拉斯定理(勾股定理)对后来的数学哲学来说,其意义非常巨大,使得人们对数学研究的视野从名数进入到常数,使得人们研究万物的本原从具体的事物中抽象为脱离了具体事物的数。数,在他是一种信仰,一种宗教。——他们以逻辑的数学思维寻求到了宇宙最根本的本质规律和本源;找到了灵魂的纯净和生命的永恒的逻辑规律,他们以自己的智慧触摸到了宇宙间上帝的指纹和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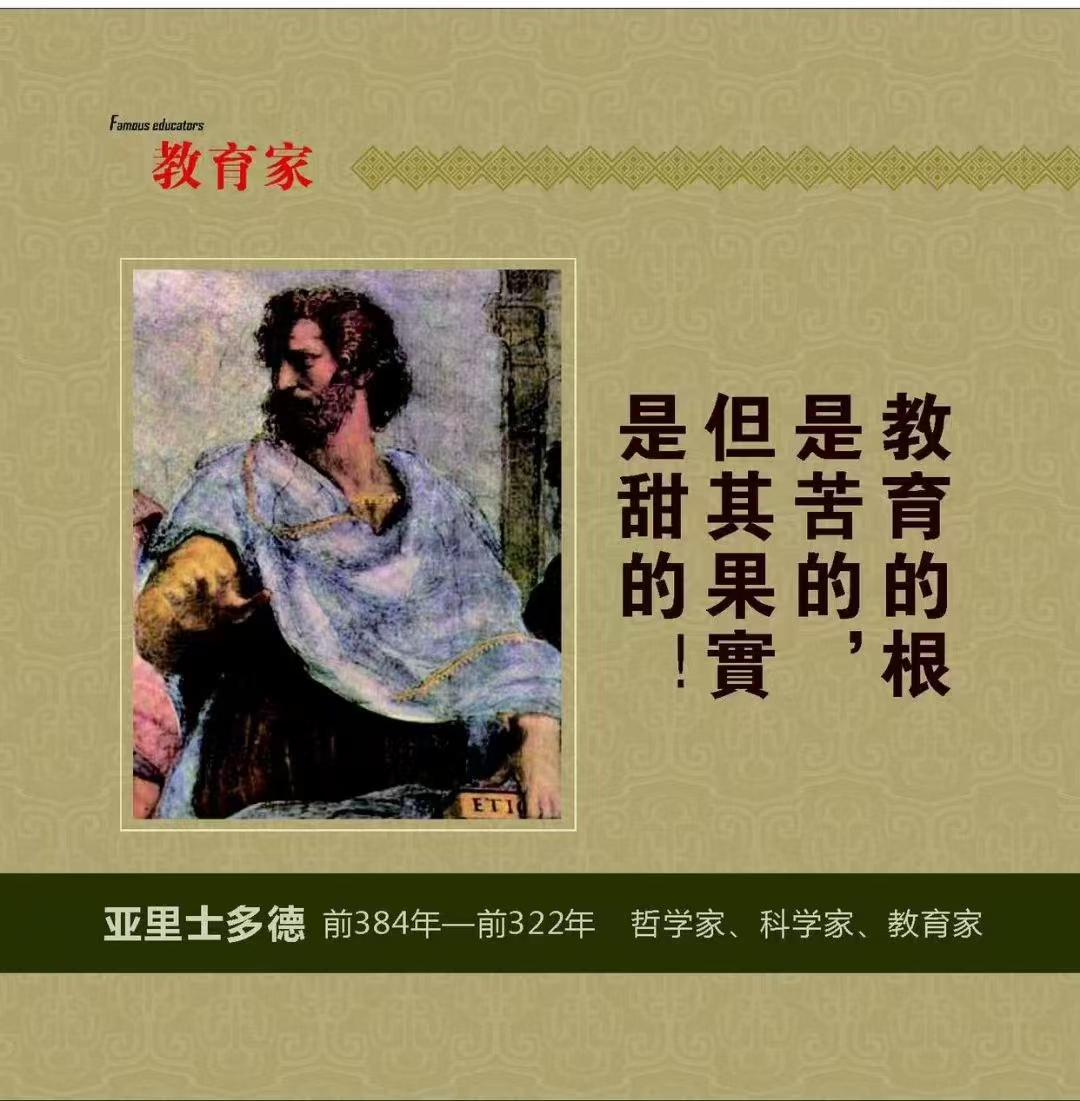
这里不能不牵扯到罗马帝国公元354年出生的奥古斯丁,他认为一切美源自天主。美是分等级的,最高的、绝对的美是上帝,其次是道德美,形体美是低级的、相对的美。低级有限的形体美本身并无独立价值,只是通向无限的绝对美的阶梯。美体现为整一、和谐,而整一与和谐是上帝按照数学原则创造出来的,因而美的基本要素是数。这个观点明显是受到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影响。在美和丑的问题上,他主张美是绝对的,丑是相对的。孤立的丑是形成美的积极因素,这种看法具有辩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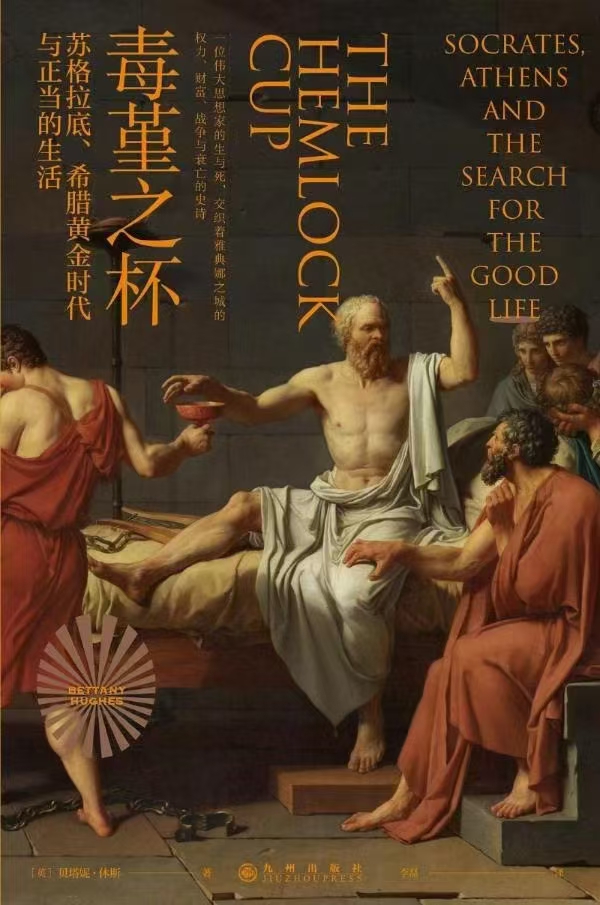
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写道:“你创造天地,不是在天上,也不在地上,不在空中,也不在水中,因为这些都在六合之中;你也不在宇宙之中创造宇宙,因为在造成宇宙之前,还没有创造宇宙的场所。你也不是手中拿着什么工具来创造天地,因为这种不由你创造而你借以创造其他的工具又从哪里得来的呢?哪一样存在的东西,不是凭借你的实在而存在?因此你一言而万物资始,你是用你的‘道’——话语——创造万有。”

这一点上,的确和中国的老子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只是“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上善若水,柔弱胜刚;反者道动,贵柔守弱;淡泊明志,知足常乐”,只是老子对此“道”的理念,仅仅存于言简意赅依然显得有点模糊,而没有更深入的展开,没有给我们开拓更广阔的视野。
老子的思想体系可以说是以形而上的道为根本依据,以“道法自然”为宗旨,以自然无为为纲纪,以依道修身为中介,以治国安民、实现社会和谐和人生理想为归宿的理论巨屋。关于社会人生和谐及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以及关于自然无为和依道治国的思想,这部分最重要的哲学和思想组成部分,没有开拓更广阔的思想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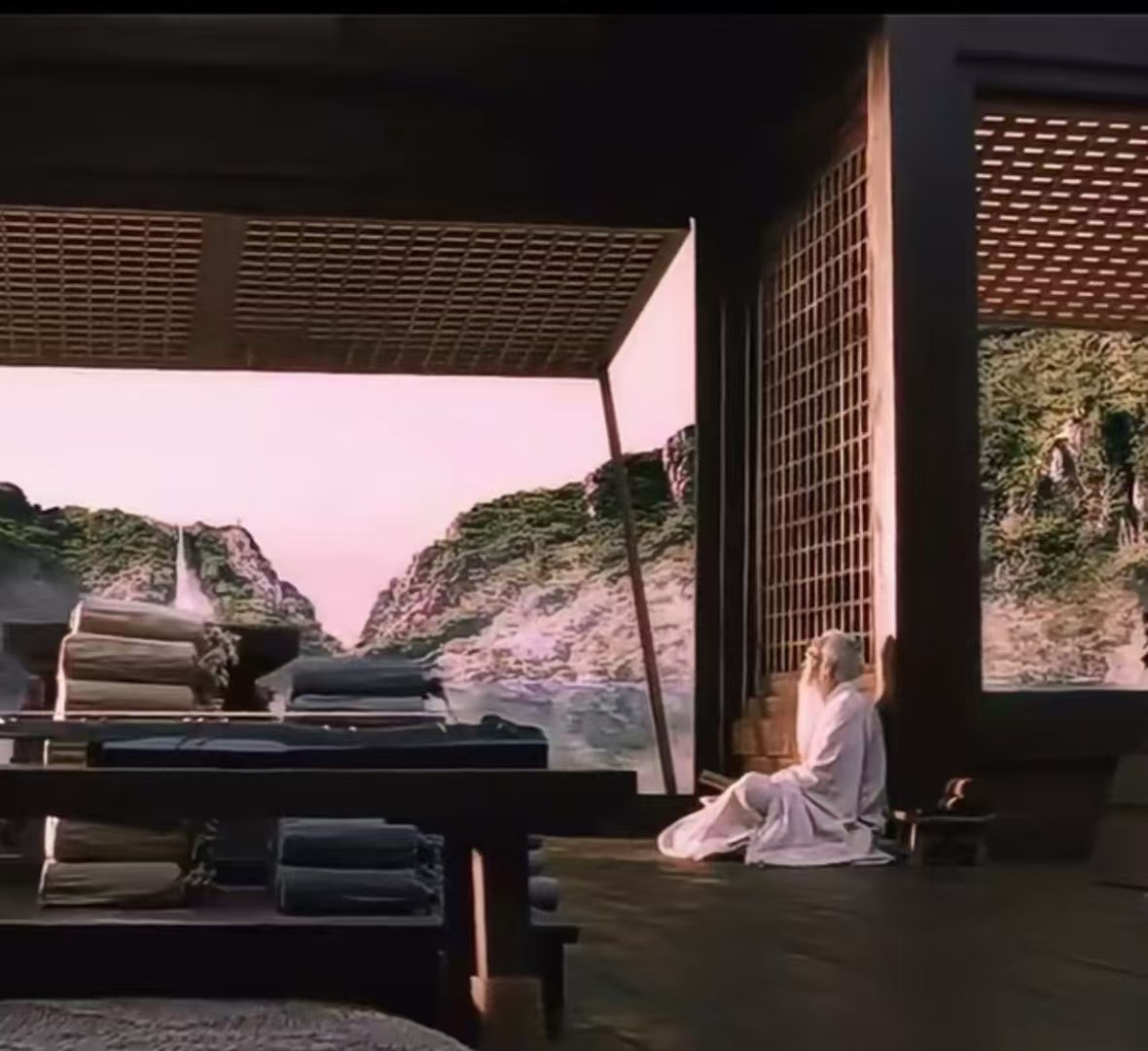
恰恰相反,后来的人们在这种纯粹理论的问题上没有太多的兴奋点,是因为我们的土壤没有促成这种思想之树根深叶茂的条件。中国先贤中有圣徒式人物吗?有,墨子。他的上天信仰与学派行为,与其他诸子相比独步一时,但在中国没有成为主流?他的“非攻”、“爱人”的确不合中国的时宜,中国的统治者和土壤都不奉行这种理论。而儒、法两家的忠君思想和清规戒律,统治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历史,儒家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最主要的思想框架,牢牢地固化了人们的思想结构,这种思想从理论到实践以及渗透到每一个细节,从君臣父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到生老病死等等,不一而足,无不寓其致治之思。

后来我们引进了佛教,又加进了中国元素,尽管“信”的人很多,善男信女比比皆是,原因是它的实用主义的门槛很底——“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如此等等的道德准则,怎么会产生崇高情怀、眼光远大、舍生取义的宗教精神和信仰力量呢?更何况至高的全人类情怀在和“儒释道”伦理面前更是格格不入。和实用主义命运与共息息相关的是另外一套社会现实的呈现。自1912年满清灭亡以后的一百多年里,社会的动荡和思想理论的繁杂,无一统一社会的整体结构和人们的系统理念。特别是我们的国度的历史命脉和前苏联息息相关,而由于前苏联的解体和文革的崩溃之后的现实,代之以生命意义的虚无主义和世纪末的废墟情绪的滋长,人们已经没有仰望一个时代崇高标杆的情怀和心理诉求,所以说,我们会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自己的本土“宗教”,这个追问似乎也已成为天方夜谭!即便像王阳明这样在现实生活中高一点、远一点、飘逸一点的思想灵魂,只是成为人们仰望的境界,而不可能成为“宗教”、“信仰”飞翔的翅膀。

在历史人物比较上,毛泽东也是一个高翔于九天之上的人,他“环球同此凉热”的理想飞轮,从他二十多岁起就飞转起来,直到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他一直在理想的高天上飞翔。他一生的工作方法始终如一,就是“群众运动”。所以他的理论很容易感染具有崇高理想和火热情怀的年轻人,文革一时在中国大地掀起的“毛泽东热”吹遍了九州方圆,像宗教一样风行,就是因为他的思想情怀燃烧了还没有被世俗的思想情怀污化了的年轻生命,青春的生命便在冲动和激情中寻找希望的光明。然而这种“群众运动”的弊病,就是容易擅发人性的弱点!它极容易把一个人的恶诱发出来,最大限度的、无所制约的擅发人性的罪恶!文革当时有外国友人当面问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不是宗教?”毛主席回答说: “是!”
对的,只有宗教,才有这样不可捉摸的力量。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具有叛逆思想、理想主义的人,更容易接受和接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人们期盼“环球同此凉热”的最高境界,通过“阶级斗争”、“消灭一切私有制”而得到整个世界的崇高理想,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共鸣!
王阳明是智者,他说自圣人以至凡人,自一人之心以达四海之远,自千古之前以至于万代之后,无所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谓天下之大本也。
王阳明对历史文化的理解,以及他的崇高美丽和在历史长河中表现出来的潇洒和风流,将日益被人们领略和仰望!人性的崇高,在这里得以眺望和追求,人类从来不会因为道路的坎坷而臣服于平庸和颓废。

我在看央视一个节目时,大学生问白岩松“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回答说:“人生没意义!”这使我非常伤痛!一个社会使命感虚无的时代,生命意义的丧失,对生命和社会意义探索的冷漠和溃退,在废墟化情调引导下的世纪末情绪,的确严重影响着社会秩序的重建和思想系统结构的重修!我们需要自我反省,需要内心系统和社会实践上的清算,认识自己的残缺和罪性,重新构建整个社会的理性信念和思想逻辑系统,在废墟之上重振信仰的力量,重建新的全人类的生命意义系统,在光明的太阳的照耀下,构建人类社会光明灿烂的理想大厦!

爱尔兰大文豪萧伯纳说:“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让我们铭记在心!


刘吾魁 |
中国著名文化学者、书画艺术家、诗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海峡两岸文化艺术产业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文化产业促进会副秘书长、人民日报《时代周刊》理事会理事、《世界名人录》特邀顾问编委;中共甘肃省委原《时代风》杂志总编。原国务院扶贫办中国扶贫开发协会研究室主任、贵州省黔南州政府文化顾问、甘肃省政法大学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甘肃省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工程创作成员、北京刘氏宗亲联谊会副主席、中国周恩来研究会秘书长、健康中国促进工作委员会国家智库专家成员、世界教科文卫组织专家成员、新加坡新神洲艺术院院士、香港科学院艺术院荣誉博士。 1980年版画《马可・波罗东游》入选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在中国美术馆出、获五年度优秀作品奖。版画《生命的启示》、摄影《魂归祁连山》分别获新世纪改革开放书画展一等奖和二等奖;书法《大林寺花》获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念展一等奖。中国画《春华》获新千年书画大奖赛特别荣誉奖。中国画《散入春光几度》和书法《毛主席诗词・菩萨蛮・黄鹤楼》由毛主席纪念堂收藏;书法《毛主席诗词•七律•答友人》由人民大会堂收藏;中国画《冬海》入编由中央美院、北京大学、首都师大主编的《今日中国美术》画典。 主编有诗集《唱给毛泽东的歌》(和吴辰旭)(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臧克家、冰心任顾问),获国际书籍展一等奖。1986年初在甘肃省委书记李子奇挂帅指导下,创作中国首部为西路军甄别的电视纪实片《血热的道路》,得到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高度评价;电视片《史诗铭刻在甘肃大地》获1991年甘肃省社会科学最高成就奖。歌曲《古战场抒怀》获1996年解放军全军战士杯二等奖、入编《中外军旅名歌经典》。为毛泽东主席的孙子毛新宇策划、创作盒带及CD光盘和MTV《爷爷曾在这里走过》;2008年为毛泽东之子毛岸青邵华夫妇策划、创作由宋祖英、杨洪基等演唱的CD光盘《永远的怀念》,并获2008第六届中国金唱片奖。(均由中国唱片总公司、广州新时代音像公司出版,人民大会堂首发)。 2011年创作油画《延水情长》获甘肃省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工程优秀作品奖。2020年创作评弹《十指连心》,获全国评弹大赛优秀作品奖;被中国曲艺家协会推荐,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学习强国》推出,中央电视台播出。2021年创作话剧《我们万众一心(和李茂林)》。 美术论文《生气勃勃的边塞画卷》介绍到多个国家;时政论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和实践纲领》,入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库》(中央党校、北京大学、团结出版社联合出版)和《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研究文集》,并被此两集评为优秀论文。领衔主编《中国扶贫十年》。其艺术生平1998年5月号英国剑桥《华人春秋》作专版介绍。生平入编《中国最具影响力艺术家》《世界华人艺术家大典》等二十几部书典。 |